
丹尼尔·耶金先生是全球能源界的“首席思想家”,近期,耶金老爷子(之所以称他“老爷子”,一是作为后辈表示尊敬,二是他确实老了,谁也扛不住岁月的洗礼)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文,深入分析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现状、问题、动向,特别是需要汲取的教训等,堪称一篇反思全球能源转型的 “标志性”文章。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因《石油风云》(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一书获得“普利策”奖并因此成为全球能源界畅销书作家和思想家以来,老爷子一直是全球能源思想界的“不倒翁”。而且他创立的“剑桥能源周”(CERAWEEK)堪称全球能源界的“达沃斯论坛”,据说刚刚结束的2025第43届CERAWEEK再创参会人数和参会层次新高。在全球能源界的“丛林”里,作为“首席思想家”动物,估计只要老爷子一发声,全球业界的大小“动物”们都要竖起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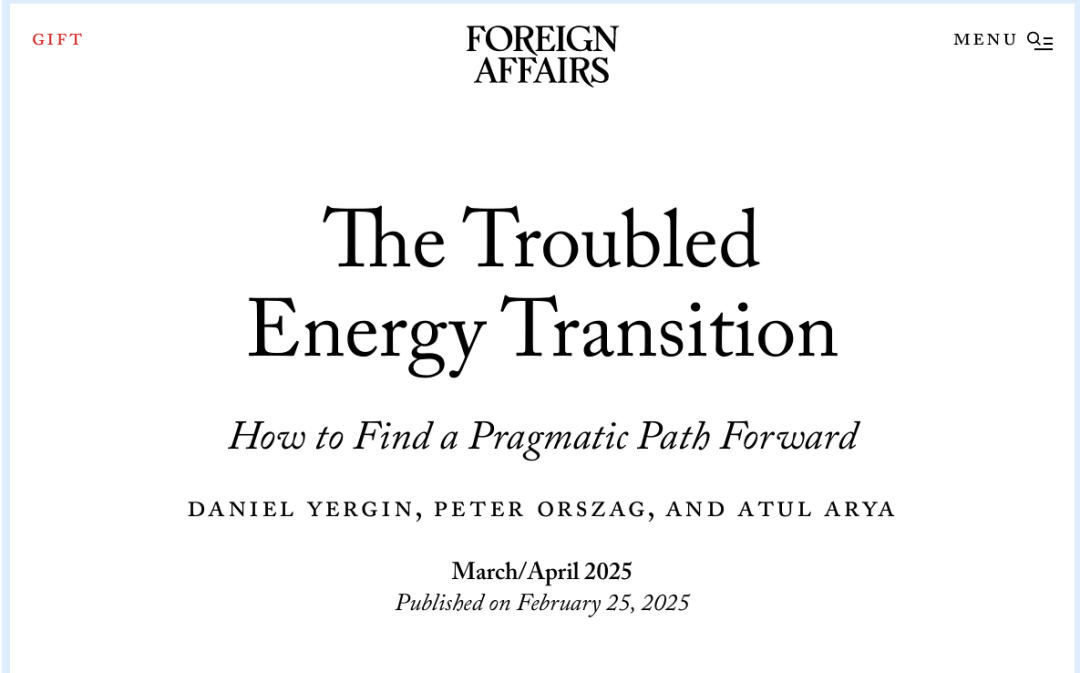
这不,最近老爷子以标普全球副主席的身份,会同其他两位专家(一位是Peter Orszag,拉扎德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曾任奥巴马政府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另一位是Atul Arya,标普全球的首席能源战略官)在《外交事务》杂志(2025年3/4月刊)的这篇反思全球能源转型的雄文又引起了广泛关注。题目是:陷入困境的能源转型——如何找到一条务实的前进之路(The Troubled Energy Transition: How to Find a Pragmatic Path Forward)。清泉并没有第一时间留意到这篇文章,而是我国某知名中东问题专家前两天给我发了一个PDF版本,说:“看了吗,耶金反思自己对能源转型的错误预测”。
看了以后,准确地说,耶金老爷子某种程度是代表全球能源思想界,对当下全球能源转型的一种反思性的总结和梳理,绝对是一篇重磅文章。其核心观点是:“全球能源转型绝对不是‘线性’的,而是多维的、迂回曲折的;而且截至目前,我们所目睹的能源转型其实并非是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而只是在化石能源消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块,因为全球能源消费总量一直在增长。”

好吧,不再狗尾续貂,清泉用了一点时间,将老爷子的这篇雄文编译如下,供大家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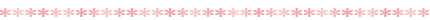
陷入困境的能源转型
——如何找到一条务实的前进之路
2024 年,全球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在不久前似乎还是不可想象的。在过去的15年里,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从几乎为零增长到占全球发电量的15%,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下降了90%。这些发展标志着全球能源转型取得了显著进展,即从目前以碳氢化合物为主的能源组合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低碳能源组合转变。
然而,另一方面,2024 年在也是创纪录的一年:石油和煤炭的消费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碳氢化合物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只是从1990年的85%下降到现在的约80%。
换句话说,正在发生的与其说是 “能源转型”,不如说是“能源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增长不是取代传统能源,而是在传统能源的基础上继续增长。
这并不是人们预期的能源转型过程。对气候变化的担忧使人们期望迅速摆脱碳基燃料。但是,全球能源系统的现实情况打破了人们的预期,从主要依靠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向主要依靠风能、太阳能、电池、氢能和生物燃料的能源系统过渡,显然要比最初预期的更加困难、昂贵和复杂。更重要的是,从过去能源转型的历史来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那些转型也是 “能源的增加”,每次都是增加而不是消除先前的能源。
因此,世界远未走上实现经常提出的到2050年实现 “净零排放 ”目标的轨道——在这一平衡中,任何残余排放都被大气中的排放清除量所抵消。实际上,截至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来实现这一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计划来提供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大量投资。国际能源署(IEA)在2021年预测,世界要实现2050年的目标,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从2020年的339亿吨下降到2030年的212亿吨;而到目前为止,排放量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2023年达到了374亿吨(没有理由认为在未来短短七年内下降40%是完全可行的)(2024年的排放量进一步上升,同比增加2.1%,清泉注)。其他事实也同样反映了转型的挑战。拜登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电动汽车占美国新售出汽车的50%;然而,这一数字2024年仍然只有10%,汽车制造商面临数十亿美元的亏损,目前正在纷纷削减对电动汽车的投资。
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成本太高:数万亿美元的成本,而谁来支付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部分问题是没有认识到气候目标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它们与其他目标——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经济发展到能源安全和减少地方污染——并存,而且由于东西方和南北方日益加剧的全球紧张局势而变得更加复杂。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分析师和活动家对转型的预期,以及相应计划的制定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理想主义色彩。
越来越清楚的是,全球能源体系的转变不会以线性或稳定的方式展开。相反,它将是多维的——以不同的速度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展开,采用不同的燃料和技术组合,受制于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并由政府和公司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需要根据复杂的现实重新思考政策和投资。因为能源转型不仅仅是能源问题,而是整个全球经济的重新布局和再造。这种反思的第一步是理解为什么转型背后的关键假设未能实现。这意味着要努力应对地缘政治、经济、政治和物质方面的权衡和限制,而不是希望它们消失。
1// 史无前例的转型
当前关于能源转型的许多想法都是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形成的,当时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量都急剧下降。这些急剧下降引发了人们的乐观情绪,认为能源系统是灵活的,可以迅速改变。IEA在2021年5 月发布的 “净零排放路线图 ”中反映了这一思路,该路线图认为,在通往2050年的道路上,不再需要对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进行投资。这种想法形成了“过渡线性”的主流理论,即许多国家将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其他一些国家将在206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如中国;印度将在207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然而,这一雄心壮志与在四分之一世纪内彻底改造价值115万亿美元的支撑全球经济的能源基础的规模和实际限制相冲突。
第一次能源转型始于1709年,当时一位名叫亚伯拉罕·达尔的金属工人发现,煤炭是比木材 “更有效的炼铁手段”。随后的“转型”至少持续了一个世纪。虽然19世纪被称为“煤炭世纪”,但能源学者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指出,煤炭直到20世纪初才取代传统的生物质能源(如木材和农作物秸秆)成为第一大能源。185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发现的石油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取代煤炭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煤炭使用量的绝对值在下降——2024年,煤炭使用量是20 世纪60年代的三倍。
今天,同样的模式正在上演。全球约30%的人口仍然依靠传统的生物质能做饭,对碳氢化合物(化石能源)的需求尚未达到顶峰,甚至还未趋于平稳。自1990年以来,碳氢化合物在能源使用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即使可再生能源出现了大规模增长(同期,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70%)。而且,预计未来几十年全球人口将增长约20 亿,其中大部分在全球南方国家。在非洲——一个人口结构年轻的大陆,其人口预计将从目前占全球人口的18%增长到 2050 年的25%——近6亿人生活在无电状态下,约10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的烹饪燃料。传统的生物质能源仍占非洲大陆能源消耗总量的近一半。随着非洲人口的增长,将有更多的人需要食物、水、住所、热能、照明、交通和工作,这将进一步产生对安全和负担得起的能源的需求。如果没有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2// 主要是经济因素
过去的转型,例如从木材到煤炭的转变,都是出于改善功能和降低成本的考虑,而目前在整个能源系统的大部分领域,这些激励因素尚未出现。转型的规模意味着成本也将非常高昂。技术、政策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使得估算能源转型的成本具有挑战性。
最近的估算来自气候融资问题独立高级别专家组,该专家组的数字为在阿塞拜疆举行的COP29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年度论坛——提供了一个框架。专家组预测,到2030年,全球气候行动的投资需求将达到每年6.3万亿至6.7万亿美元,到2035年将增至8万亿美元。报告进一步估计,从现在到2030年,全球南方国家将占平均增量投资需求的近45%,而这些国家在满足其融资需求方面已经落后,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根据上述估算,从现在到2050年,能源转型成本平均每年约占全球 GDP的5%。如果南半球国家基本不受这些财政负担影响的话(需要靠发达国家资助),那么北半球国家每年的支出将占到GDP的10%——以美国为例,超过国防支出占GDP比例的三倍,大约相当于美国政府在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和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上支出的总和。这些成本反映了化石燃料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遍存在——不仅仅是石油和天然气,还包括水泥、塑料和钢铁的生产——以及比尔·盖茨所说的 “绿色溢价”,即低排放技术比高排放技术更加昂贵。
换句话说,要实现净零排放,还需要对从全球北方流向全球南方的资本流动进行前所未有的重组,这就需要对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56%的低收入国家 “处于高度债务困境”。虽然创新的融资机制(如以债务换气候和以债务换自然)会有所帮助,但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评级较低,成为外部投资的主要障碍,并提高了资本成本。因此,大部分财政负担将由发达经济体承担。但即使在发达经济体,债务也大幅增加——目前平均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100%,这是自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也严重制约了政府通过公共开支为转型提供资金的能力。
无论是通过某种直接或隐含的碳价格,还是通过监管要求,期望资产经理或投资顾问自愿将资金转向有利于转型的投资,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奏效。毕竟,资产管理者有遵循资产所有者(如养老金计划或保险公司)指示的信托责任,而美国的ESG 基金(那些投资于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实践的公司的基金)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回报不佳而出现了资本外流。
3// 能源不安全
下一个挑战是能源安全,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受到重视。尽管疫情提出了其他更迫切的需求,但俄乌战争以及随后对全球能源市场的破坏又将这一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甚至在战争爆发前的2021年11月,美国政府就已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解决拜登总统所说的 “高油价问题”。从那时起,美国已经从战略储备中提取了近一半的石油来应对价格冲击(尽管已经开始适度补充)。
突然措手不及的欧洲各国政府也采取了自己的措施。在俄罗斯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后,德国总理舒尔茨飞往加拿大,敦促其增加天然气供应。柏林提议为新的天然气发电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以平衡风能和太阳能的间歇性发电,维持电力供应。
各国政府根本无法容忍能源供应中断、短缺或价格暴涨。因此,如果政府想让其选民接受转型,能源安全和可负担性是至关重要的。否则,针对能源和气候政策的政治反弹就会出现——在欧洲被称为“绿色反弹”——其影响正在选举中显现。确保公民能够及时获得能源和电力供应对于人民的福祉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要认识到,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组合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时间将比几年前预计的要长,这就需要在碳氢化合物供应和基础设施方面持续进行新的投资。
事实上,在如何平衡气候优先事项与经济发展需求的问题上,已经出现了新的南北分歧。这是重新思考能源转型的速度和形式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全球南方,能源转型与经济增长、减贫和改善健康等当务之急相互对立。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能源安全、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不可能三角”问题与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截然不同。正如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所说,“‘转型的需要’必须与‘生存的需要’相平衡,以确保我们目前在提供教育、医疗和基本基础设施方面消除贫困的政策不会因为他人的指令而受挫,因为他人的指令没有充分考虑到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目前,发展中世界近一半的人口—30 亿人—每年的人均用电量低于美国冰箱的平均用电量。随着能源使用的增长,“碳化”将先于“去碳化”。天然气是一种现成的选择,它是煤炭以及产生有害室内空气污染的传统生物质燃料的更好替代品。尽管全球石油需求似乎将在 2030年代初趋于稳定,但天然气消费预计将在2040年代继续增长。到2040年,液化天然气的产量有望增加65%,从而满足欧洲的能源安全需求,取代亚洲的煤炭,并推动全球南方的经济增长。
例如,在印度最近的预算中,对经济增长的偏好就很明显,印度约75% 的电力依赖煤炭。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承诺 “能源转型之路”将强调就业和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必要性”。这一点在人均收入为1300美元的乌干达也很明显,该国的目标是建设一条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输油管道,从艾伯特湖油田通往坦桑尼亚的一个港口,以便向全球市场销售石油。乌干达政府将整个项目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却遭到了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强烈批评和反对。
在碳关税问题上,南北方在优先事项上的冲突尤为突出。作为减排努力的一部分,许多全球北方国家的政府设置了障碍,阻止其他国家走与它们实现繁荣相同的碳基经济发展道路。欧盟已经启动了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的第一阶段计划。CBAM旨在支持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气候目标,首先根据钢铁、水泥、铝和化肥等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对这些产品征收进口关税,然后扩大到更多的进口产品。全球北方的批评者认为,由于供应链的巨大复杂性以及追踪进口产品中的内含碳量的相关困难,这些措施将是无效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批评者则认为CBAM阻碍了他们的经济增长。印度经济事务秘书Ajay Set认为,CBAM将迫使印度经济承担更高的成本:“印度的收入水平只有欧洲的二十分之一,我们能承受更高的价格吗?不,我们不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CBAM 及其规定的复杂繁琐的排放报告,更像是世界富裕地区利用碳关税将其价值观和监管体系强加给需要进入全球市场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
政策不对称在排放目标中显而易见: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占能源相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近45%。它们都没有2050年的净零排放目标;它们的目标是2060年或2070年。同样,虽然全球新建燃煤电厂的投资持续下降,但2023年开始的7500万千瓦(75吉瓦,GW)新建煤炭发电装机几乎全部在中国。印度雄心勃勃地计划到2030年发展50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远高于迄今为止的190吉瓦装机容量(与2023年的18吉瓦装机容量相比需要大幅增加),但印度还承诺在2024年至2030年期间投入670亿美元扩大国内天然气网络,并计划到2032年将煤炭装机容量至少增加54吉瓦。
4// “大石头”(关键矿产)
采矿和关键矿产的复杂性是制约能源转型步伐的另一个主要因素。IEA预测,到2040年,全球对“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矿产的需求将翻两番。其中最重要的是锂、钴、镍、石墨和铜等关键矿物。仅在2017 年至2023年期间,锂的需求量就增加了266%;钴的需求量增加了 83%;镍的需求量跃升了46%。标准普尔预计,在2023年至2035年期间,锂的需求量将再增长286%;钴的需求量将增长96%;镍的需求量将增长91%。电动汽车对铜的需求量是内燃机汽车的两倍半到三倍;电池存储、海上和陆上风能系统、太阳能电池板和数据中心都需要大量的铜。标准普尔对未来铜需求的分析表明,到2030年代中期,全球铜供应量必须增加一倍,才能满足当前的政策目标,即到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是极不可能的,因为根据标准普尔对全球自2002 年以来投产的127个矿山的跟踪数据,开发一个大型新矿山需要 20 多年的时间;在美国,平均需要29年。
另一大障碍是当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反抗。例如,塞尔维亚于2024年7 月与欧盟签署了一项开发Jadar项目的协议,该项目将为欧洲电池价值链和电动汽车生产90%的锂离子电池。然而,2024年8月,该协议导致数万人走上贝尔格莱德街头游行;反对派领导人之一称该项目是“绿色转型与专制主义的绝对合并”,并补充说它可能会打开“通往新殖民主义的新大门”。这种反对派做法将环保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团结在一起,而俄罗斯在欧洲选举中部署的同类虚假信息则强化了这种反对派立场。一年前,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导致一个占巴拿马国内生产总值5%的铜矿被关闭。抗议活动的支持者之一称赞反对派挫败了“巨大的采掘资本野兽”,并称这为其他国家的抗议活动树立了榜样。在美国,内华达州的Thacker Pass锂项目在获得美国联邦政府22.6亿美元贷款后,初步计划于2026年投产。
简而言之,推动能源转型的矿产与当地的环境、政治、文化、土地使用问题以及许可障碍之间存在着矛盾。能源转型需要找到解决这一固有矛盾的方法。
5// 竞争的复杂性
地缘政治竞争是另一个复杂因素。能源转型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日益交织在一起。不仅在实施目标方面如此,在 “绿色供应链”方面也是如此。
中国已在采矿业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将矿物加工成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所必需的金属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稀土开采量占世界总量的 60%以上(美国仅占9%),稀土加工和提炼量占世界总量的90%以上。中国的石墨产量占世界总量的77%,加工量占世界总量的98%,锂和钴的加工量占世界总量的70%,铜的加工量占世界总量的近一半。
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将这种主导地位扩展到其所谓的“全球新能源产业链”,在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将大量资金投入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由于中国规模庞大、成本低廉,中国政府将这一努力描述为发展和主导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广泛综合方法。从2000年到2022年,中国为65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的能源项目发放了225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约75%用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发。从2016年到2022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的能源项目融资超过了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任何一家西方支持的主要多边开发银行。
美国一心想保护自己的绿色供应链,因此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产业政策举措和大规模投资,并对半导体征收关税、实施限制和管制,以“双重用途”为由禁止向美国出口稀土——这与美国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的理由如出一辙——因为稀土被用于可再生技术和国防工业。特朗普政府很可能计划对中国进一步征收关税。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减缓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增加成本,并限制能源转型的步伐。目前,各国政府正在动员“多元化”和 “去风险”供应链。但在实践中,由于成本、基础设施限制、所需时间以及项目获批所面临的巨大障碍,这证明是非常困难的。
6// 电力激增
去年,能源转型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在全球需求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充足的电力供应。这是四重叠加的结果:“能源转型需求”(如电动汽车)、重整和先进制造业(如半导体)、加密货币挖矿以及为人工智能革命提供动力的数据中心对能源的“贪得无厌”,都会导致消费激增。据估计,到2030年,仅数据中心每年就会消耗美国发电量的近10%;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每三天就会开设一个新的数据中心。
电气化趋势表明,从现在到2050年,美国的电力需求将翻一番。电力消费已经超过了近期的需求预测。负责管理从伊利诺伊州到新泽西州电力传输的PJM公司在2022年到2023年期间的增长预测几乎翻了一番,并警告说在本十年结束前将出现电力短缺的危险。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到2035 在美国实现零碳电力的目标将比COVID停产后的萧条时期显得更具挑战性。
事实上,除了电池之外,天然气在发电中发挥的作用显然比两三年前预测的还要大。公用事业规模的天然气发电每千瓦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煤炭少60%。美国对天然气的依赖也在迅速增长。2008年,煤炭发电量占美国发电量的49%;为促进能源转型,到如今美国国内发电总量中,天然气发电量占48%,风电和太阳能占27%。即使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断增长,天然气仍将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
7// 转型折衷
近年来,一些推进能源转型的重大举措已经成形,从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和欧洲的《绿色交易》,到呼吁 “以公正、有序和公平的方式摆脱化石燃料”的COP28迪拜共识。然而,越来越清楚的是,政府和私营部门需要在平衡能源获取、安全和可负担性的同时,引导能源转型。美国以外的投资者、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将在白宫优先事项发生明显变化(指特朗普能源政策优先事项已从可再生能源转到传统能源)的环境下开展这项工作。
第一步是明确“抵消”的性质和面临的挑战,正如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警告的那样,不要“斥责线条不直”。在这种情况下,线不会是直的,所以认识到这一点比斥责更好。
在保护主义抬头之际,各国政府都在努力“降低”供应链的风险,将其引向本国或更靠近本国的地方。未来几年能源需求和流动的结构调整将在降低成本与多样化和保护国内产业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建立支持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所需的供应链,需要政府之间以及与私营部门的协调,以改善物流和基础设施、许可程序、技术流动、金融和人员培训。随着这些供应链在未来的重新配置,它们必须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地域集中的。例如,美国和欧盟除了将能源制造业转移到国内之外,还应与亚洲盟国合作。
另一个取舍与清洁能源技术所必需的采矿和加工有关。当今冗长的许可和监管审批流程威胁着能源转型所需的矿产供应。对新矿山的投资往往不符合私人投资者和多边开发银行所使用的各种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从而限制了资本流动,造成进一步的瓶颈。一致的标准必须解决环境问题,同时加快对所需矿产新矿的投资。
任何减排之路都必须经过全球南方,因为那里是能源需求大幅增长的地方。然而,南半球国家在吸引必要资金以摆脱廉价的煤炭能源(或木材和废料能源)方面面临着特别严峻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可再生能源项目通常需要高昂的前期资本成本,因此需要长期的私人投资来增加流向南半球的资金。
自从三个多世纪前亚伯拉罕·达尔比将木材改为煤炭以来,技术创新一直是能源生产每一次演变的核心。对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研发和应用推动了太阳能和风能成本的大幅下降。然而,除了电力之外,终端用途也需要新的低排放和零排放技术。在美国,《两党基础设施法》(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CHIPS 和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以及《通货膨胀削减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共同旨在加速可再生能源的增长、电动汽车的部署和能源创新,包括使碳捕集与封存、氢和大规模电力存储等技术具有商业可行性。但现在要确定特朗普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削减和调整这些计划还为时尚早。如今引人注目的是,人们重新支持核能的作用,包括现有技术和先进技术,认为这是过渡战略和可靠性的必要条件。这反映在对核裂变和核聚变技术的公共和私人投资的增长上。但同样需要的是对新技术的投资,而这些技术如今可能只是某些研究人员眼中的闪光点。
今天的能源转型与以往的能源转型有着本质区别:它是变革性的,而不是叠加性的。但迄今为止,它只是“补充”,而非替代。与能源转型相关的挑战规模大、种类多,这意味着能源转型不会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或以线性方式进行:它将是多层面的,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技术组合和不同的优先事项进行。这反映了作为当今全球经济基础的能源系统的复杂性。这也清楚地表明,这一进程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展开,对传统能源的持续投资将是能源转型的必要组成部分。线性过渡是不可能的;相反,过渡将涉及重大权衡。同时解决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能源获取问题的重要性凸显了走更加务实道路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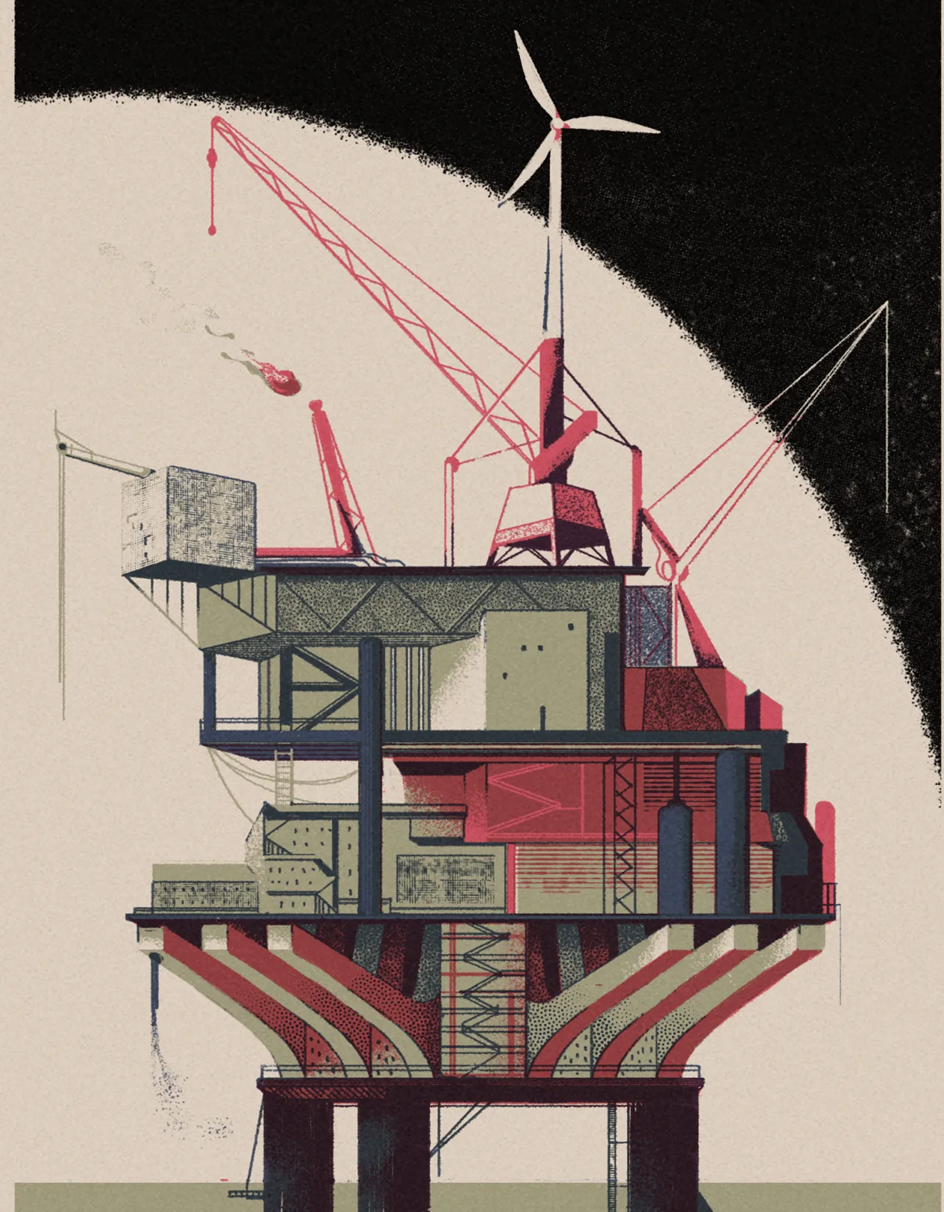
以上是耶金先生的全文。这应该是老爷子经过至少大半年的梳理和系统思考后的对全球能源转型的综合性评述。因为文中观点与2024年12月他来北京参加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和标普全球(S&P Global)联合举办的第11届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时在主旨演讲中的观点如出一辙。那次演讲中,他强调:
“能源转型不仅仅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是一个核心话题,对于全球的经济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也都是重中之重,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它的概念。过去几年的能源转型概念基本都是在疫情期间所形成的,疫情期间价格下滑,需求下降,可是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我们要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历史告诉我们,看待能源转型的单向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你只是画一个直线,一直延伸到2050年,然后就突然之间实现转型,这种方法是不会发生的,也不可能发生的,能源转型不会是一条直线,它甚至不会是一个线性的发展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谈所谓的多维能源转型,你可能会说什么是多维能源转型?答案就是我尝试着给大家提供答案,那就是它会以不同的速度,利用不同的技术,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优先事项,有不同的时间表,以这种形式而发生,能够满足一个国家需求的,或者说一个国家所能够承担的和另一个国家截然不同。”
可以看出,以上这段话与老爷子这篇文章的观点如出一辙。
看来,在“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的矛盾情境下,务实转型、先立后破、因地制宜等策略,将成为各国、各地区、各企业的理性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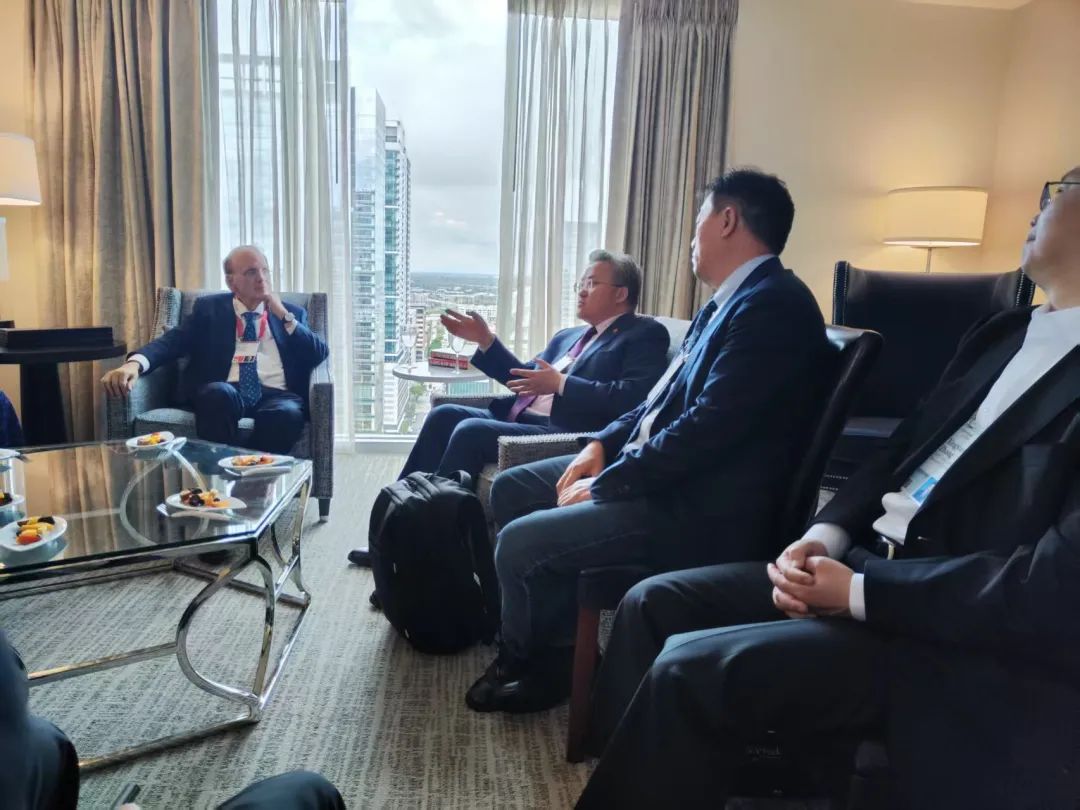
(2024年3月,剑桥能源周参会期间,耶金先生与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团队的会面)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