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苏珊·斯特兰奇是谁?这么说吧,她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奠基人之一,是国际关系理论中“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为数不多的堪称世界级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尤其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界,斯特兰奇女士与美国的罗伯特·吉尔平号称全球这个领域的“双子星”。罗伯特·吉尔平的代表作在此前的微文里介绍过,有《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等;斯特兰奇女士则写出了《国家与市场》《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等传世之作。
如果仅用一本书来见证斯特兰奇女士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成就,那无疑就是《国家与市场》(States and Markets)了。本次微文就说说这本书,其核心就是“结构性权力”。
1. 苏珊·斯特兰奇和她的《国家与市场》
苏珊·斯特兰奇(1923~1998)是英国人,她是个“大器晚成”的学者,学术生涯一开始并不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她为外界所知、具有国际声望,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遗憾的是,她在1998年因病去世,整个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仅有20年。这一点,她不如罗伯特·吉尔平,吉尔平活到88岁,直到2018年才离世,其学术生涯的黄金期接近半个世纪。但这不妨碍斯特兰奇成为伟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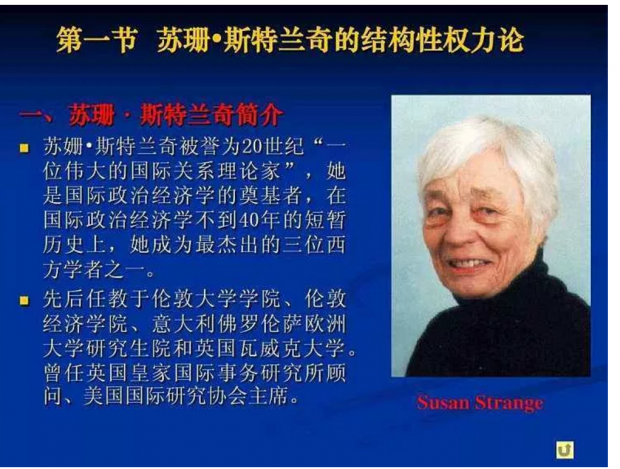
斯特兰奇当过英国《经济学家》和《观察家报》记者,在伦敦的大学学院教授过国际关系,后来到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1978年起先后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生院等院校担任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历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顾问,英国国际问题学会会长,以及总部在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会长等职。1970年在《国际事务》杂志发表《相互忽视的国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一文,最早明确提出要从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视角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强调寻求一种新的分析世界经济的方法,代表作便是《国家与市场》。
在《国家与市场》这本书中,斯特兰奇深入浅出地评价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基础和主要流派的观点,特别是提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区别,用四个基本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以及四个次级结构——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关系,剖析国际上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比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代表作更具有理论概括功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杂志称赞斯特兰奇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有创意的学者”,《国家与市场》这本书“又一次展现了她细致的分析和新鲜深刻的见解”,《国际事务》杂志的书评也认为“读完此书令人视野忽然开朗”。
2. 结构性权力与联系性权力
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是与联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 )相对应的。斯特兰奇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力有两种——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而且,二战以来,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竞争,结构性权力越来越比联系性权力重要。
读完《国家与市场》,结合清泉自己的理解,可以认为,所谓联系性权力,就是“传统权力”,也就是甲方靠权力迫使乙方去做或许他本来不想干的事,这种权力体现在对事情过程或结果的控制力上。比如,1940年,德国靠“联系性权力”迫使瑞典允许德国军队穿过它的“中立”领土;再如,上世纪80年底,美国凭借它对巴拿马的“联系性”权力,支配了巴拿马运河的航行条件。可以看出,所谓联系性权力是一种“绝对性”权力,是权力施动者以绝对权力压迫权力受动者做它不相干的事情。绝对性权力的背后是霸权,是“同意即生存、不同意即死亡”的强盗逻辑。在国际政治中,联系性权力就是运用军事政治的强制手段迫使别国就范。
而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士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里活动”。通俗地说,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式方法的权力。二战以来,由于国际体系、国际机制、国际组织的建立和完善,结构性权力主要指确定议事日程的权力和“设计”支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惯例、规则和国际机制的权力。这是美国学者的观察和判断。比如,中国加入2001年加入由美国当年设计、倡导和构建的WTO系统,则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必须接受体现美国人意志的结构性权力。
而斯特兰奇的观察是:结构性权力一是存在于能够控制人们的安全(即威胁人们的安全,或保护人们的安全,特别是保护人们免受暴力的侵犯)的人那里;二是存在于能够决定和支配商品和劳务生产(这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方式的人那里;三是存在于能够控制信贷供应和分配的人(机构)那里,信贷的背后是对金融资本和投资资本的控制;四是存在于掌握知识(包括思想、宗教、哲学等)、能够全部或局部地限制或决定获得知识的条件的那些人手里。这就是斯特兰奇认为的第一层级机构性权力的四个来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
斯特兰奇为什么会选择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作为结构性权力的四大来源,而不是其他?其背后是人类社会对生命、财富、秩序、公正和自由这五大要素的重视和渴望,这五大要素可谓“元要素”。无论是过去的罗马帝国、还是现在的全球一体化下的“地球村”,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前苏联)还是中国,这五种要素均是最根本的、共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意识形态,这五种要素的先后顺序和比例组合不同。而这五种要素中的生命(于国家而言,则是民族的存亡)就是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中的“安全”,财富就是“生产和金融”,秩序、公正和自由则可以综合为“知识”(还可加上“信息和网络”,由于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88年,那时互联网在全球尚未兴起)。这个意义上,斯特兰奇将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视为结构性权力的四大来源,则是其无与伦比的对人类基础性需求的洞察能力。
另外,对于结构性权力,斯特兰奇特别强调,这四种相互影响的结构来源并非国际体系或全球政治经济所特有,在人类很小的集团,例如家庭或边远乡村的社区中,结构性权力的来源同它在大世界中是一样的。说到底,这就是对安全的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贷和控制以及对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
如何进一步区分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斯特兰奇认为,四种结构性权力通常碰到的情况是,权力拥有者能够改变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又不明显地直接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做出某个决定或选择,而不做出别的决定或选择。这种权力是不大“看得出的”。这就是权力的“结构性”。只要身处这样的结构,受动者就会“自然而然”地按照施动者的意愿去做。
斯特兰奇还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帮助我们理解结构性权力:当母亲或父亲说,“如果你是个好孩子,肯努力学习的话,我们将给你一辆自行车作为你的生日礼物”,这个男孩仍可以在努力学习和与朋友玩耍之间自由选择。但是父母在家庭预算方面的结构性权力,会使孩子在权衡选择时“自然而然”地偏重与努力学习。
还有一个更加到位和经典的例子是,比如,我们说“这个男人比这个女人有权”,如果理解为“这个男人可以一拳把这个女人打倒在地”,则这个男人拥有的是“联系性权力”;而大多情况下,在现代社会,该男子在家庭和社会的结构性权力使得男子拥有社会地位、法律和家庭经济控制权,他无需扬言将不听话的女人打倒在地就可以对女人颐指气使了。
可以看出,结构性权力部分来自思想(最经典的莫过于伊朗伊斯兰革命霍梅尼的案例,1979年1月,霍梅尼在法国,通过录音带对伊朗民众“隔空喊话”,宣传他的思想,不费一兵一卒,就把伊朗巴列维国王的君主政权推翻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历史上最常见的就是僧侣和贤哲常常运用知识(思想)的权力来左右国王和将军),部分来自强制力量(军事威慑力),部分来自财富,部分来自对生产要素的分配。
如果有哪位世界级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与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有异曲同工之处的话,那就是肯尼斯·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了。各类行为体身处一个结构或体系之中,除非它退出该体系或置身体系之外,否则就要受到体系“江湖”的约束,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继续这种类比的话,“联系性权力”有点类似汉斯·摩根索的“权力现实主义”了。
除了上述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基本结构性权力,斯特兰奇在书中还提出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这四种次级结构。也就是:世界主要跨国运输体系、贸易体系、能源供应体系、跨国福利和发展体系。这四种次级权力体系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是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基本结构权力的辅佐,都受到后者的制约。书中,斯特兰奇对跨国能源生产与供应的重要性进行阐述,其核心就是国际石油政治经济,也就是,石油权力在公司、政府和市场中的转换。
3. 斯特兰奇与国际石油政治经济
无论是苏珊·斯特兰奇,还是罗伯特·吉尔平,均对跨国石油公司在国际石油政治经济的影响有深入的研究。
清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多资深甚至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包括欧美的学者所著的经典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书籍,当他们论述石油政治、国际石油机制或跨国石油公司时,往往在其著作中只是一个章节,一笔带过。但苏珊·斯特兰奇和罗伯特·吉尔平是例外。很少有像苏珊·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那样对石油公司与产油国互动的深入描述,也很少有像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里那样对跨国石油公司有着系统的解读。也许,这是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缺乏石油行业的专业知识导致的。石油行业是一个专业门槛较高的行业,这限制了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对石油政治、中东石油政治进行深入的解读和模式的建构。
慢慢地,清泉也发现,其实国际石油公司(跨国石油巨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经常应用的案例分析对象,甚至是唯一的对象。道理也不难理解,所谓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分析“权力”(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和“财富”(经济的本质就是财富)的关系,而能够把权力和财富完美结合起来的,体系政府、市场和公司三者之间“爱恨情仇”的,似乎也只有国际大石油公司了。
特别是在《国家与市场》这本书中,斯特兰奇利用国际石油政治经济发展的脉络,来解读公司、政府和市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让清泉有茅塞顿开之感。且看斯特兰奇是如何划分过去100多年国际石油政治经济的演变的:
第一阶段(现代石油业诞生—一战):在石油业发展的初期,市场实际上被美国所占领,唯一说话有分量的政府是美国政府、唯一说话有分量的公司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主要的玩家是英国和美国,主要的公司是标准石油、英国BP公司和壳牌公司。
第二阶段(一战至1960年OPEC成立):跨国石油公司来左右一切。资源国彼时都很贫穷,缺乏资金、技术、管理和销售渠道,没有力量来自己接管石油产业。彼时,英国和法国作为一战战胜国,在谋划如何在中东分赃;彼时,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共和党人柯立芝(Coolidge)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支持美国石油公司提出的在中东有权分享租让地的要求。二战大大改变了中东各国的均势和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均势,英法实际上撤出了中东,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开始崛起。美国政府和大石油公司暗中达成了交易:只要它们的利润由于开发石油,足以确保石油越来越多的供应,满足欧洲和日本不断增长的需求,那么它们可以继续自由地处理在美国以外地方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中东各国的关系。
第三阶段(上世纪60年代):从第三世界角度看,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是在市场—公司—国家的博弈中似乎是一个新的、截然不同的阶段。期间,OPEC的成立。1973年欧佩克虽然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53.5%,但是它左右市场的力量仍然是极小的。只有当欧佩克的成员国在领土范围内对所发生的事情运用政治权力时,它与公司以及与市场的力量平衡才发生巨大变化。
第四阶段(上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69~1973这几年):政府、公司和市场(市场主要的代表者是消费国,其标志是国际油价)三方的讨价还价关系开始了。这一阶段主要是国家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公司似乎失去了对市场(价格)的控制,而市场开始听从国家政策的指导。当然,在这个新阶段也不仅仅是OPEC生产国的政策其决定性作用,消费国政府同样发挥了作用。其间,美国政府企图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石油消费组织与OPEC相抗衡,这一组织就是IEA。
第五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现在):市场发挥举足轻重的作业。虽然回归到基于市场的“自由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石油公司和政府完全失去了影响。石油公司依然控制着勘探技术、海外生产、原油加工和销售。只要仍然存在着变化无常的世界石油市场,只要主要石油公司名列前10个或20个跨国企业之中,国家—市场—公司复杂的三角平衡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下去。资源国政府,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发现它们在与外国石油公司讨价还价时,不得不因为公司对技术(特别在勘探和产品开发方面)的控制而做出让步。

除了《国家与市场》这部经典以及上面提到的《权力的流散》,斯特兰奇的著作还有:《英镑与英国政策》(1971)、《赌场资本主义》(1986)、《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1988)、《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1991)等。
总之,斯特兰奇在本书中充分肯定跨国公司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和世界体系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国际石油公司,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对象。这就启发中国的跨国公司,特别是跨国石油公司,要在中国复兴和崛起的过程中,为中国贡献更多的“结构性权力”。
获得结构性权力的前提是参与进去。虽然现在我们依然只是游戏的参与者,但参与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终会变成规则的制定者。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